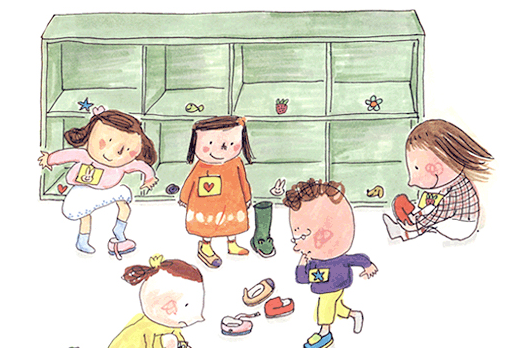无可否认,“性吧”的初衷是好的——想让消费者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谈性,了解性,接受性教育,但其可操作性有多大却值得怀疑。
仔细看看“性吧”的性教育服务项目,无非是为公众提供一些与性有关的书刊,播放一些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性教育投影,另外,还可以提供一些性健康知识网站的网址。
我们不能说这些服务对性教育毫无作用,但即便有,作用也不会太大。试想,如果真有需要,这些东西在书店、影像店都能买到,甚至在家里都可以上网看到,没必要非得长途跋涉专程跑到“性吧”吧?退一步讲,即便有人来,他们又能看出什么、学到什么呢?俗话说,一百个人看《哈姆雷特》,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。同理,由于缺乏专家的专业指导以及每个人的“性趣”不同,一百个人看同一本性教育书刊,就可能看出一百种不同内容,他们未必就能接受到真正的性教育。
其实,“性吧”惨淡经营的现状已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了。中国人现在不是不能谈性,但谁会厚着脸皮开口说“我们今天去性吧怎么样”?朋友、亲人间谈,尚且有忌讳,何况是陌生人——在咖啡吧里,与陌生人聊天是常见的事。但假如你正在“性吧”里喝咖啡,一个陌生人突然对你说“我们谈谈性好吗”,你会想到什么地方去呢?如果是异性,那谈话的性质就极有可能发生改变了。如此,谈性的不愿来,愿来的不谈性,性吧门庭冷落也可想而知了,它所标榜的性教育又从何谈起呢?
性,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还是一个比较朦胧和隐私的话题。我们提倡全民性教育的开展,但教育形式应该尊重公众的传统习惯。在笔者看来,当前最需要接受性教育的群体是在校学生和已经步入社会的中青年。对于学生而言,我们完全可以把性教育写进教程,通过教师系统的讲解,让学生对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知;而对于社会上的中青年人群来说,则可以开设一些有关性知识的专业讲座和电视节目,或者鼓励一些医院或专家设立性知识咨询热线,通过专家的权威解答来帮助公众拨开性的迷雾与困惑。而这些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,显然是“性吧”所无法企及的。如此看来,“性吧”这种看似新颖的教育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,也显然无法承担起性教育这样的重任。
仔细看看“性吧”的性教育服务项目,无非是为公众提供一些与性有关的书刊,播放一些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性教育投影,另外,还可以提供一些性健康知识网站的网址。
我们不能说这些服务对性教育毫无作用,但即便有,作用也不会太大。试想,如果真有需要,这些东西在书店、影像店都能买到,甚至在家里都可以上网看到,没必要非得长途跋涉专程跑到“性吧”吧?退一步讲,即便有人来,他们又能看出什么、学到什么呢?俗话说,一百个人看《哈姆雷特》,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。同理,由于缺乏专家的专业指导以及每个人的“性趣”不同,一百个人看同一本性教育书刊,就可能看出一百种不同内容,他们未必就能接受到真正的性教育。
其实,“性吧”惨淡经营的现状已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了。中国人现在不是不能谈性,但谁会厚着脸皮开口说“我们今天去性吧怎么样”?朋友、亲人间谈,尚且有忌讳,何况是陌生人——在咖啡吧里,与陌生人聊天是常见的事。但假如你正在“性吧”里喝咖啡,一个陌生人突然对你说“我们谈谈性好吗”,你会想到什么地方去呢?如果是异性,那谈话的性质就极有可能发生改变了。如此,谈性的不愿来,愿来的不谈性,性吧门庭冷落也可想而知了,它所标榜的性教育又从何谈起呢?
性,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还是一个比较朦胧和隐私的话题。我们提倡全民性教育的开展,但教育形式应该尊重公众的传统习惯。在笔者看来,当前最需要接受性教育的群体是在校学生和已经步入社会的中青年。对于学生而言,我们完全可以把性教育写进教程,通过教师系统的讲解,让学生对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知;而对于社会上的中青年人群来说,则可以开设一些有关性知识的专业讲座和电视节目,或者鼓励一些医院或专家设立性知识咨询热线,通过专家的权威解答来帮助公众拨开性的迷雾与困惑。而这些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,显然是“性吧”所无法企及的。如此看来,“性吧”这种看似新颖的教育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,也显然无法承担起性教育这样的重任。